那年那镇上的故事
我是一只水鬼,没有温度的水鬼,或你可以说我只有冰冷的感知。我当然不是一出生就是水鬼(水鬼应该不能生孩子的吧,又不是水果。不过我其实也不清楚,得要去问问水鬼部落的长老才能告诉你答案),但水鬼也做了将近七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对了,顺道告诉你一点,我们水鬼的时间计算与人类的一样,所以民间故事有什么到了海底生活几年后回到陆地就已过百年,那都是骗小孩的,不然我都不能站在这里说故事了。
我生前很喜欢老街,总觉得那古老的街道上蕴含着一股气味(啊,是那煎鱼的香味,我最爱了)就是不那么一样。如果你一定要我为老街找个譬喻,那它一定得是个女人,而且要是个刚生育过后的女人,或是怀里依偎着孩子的母亲。如果你觉得那样一个女人的岁数跟老街配搭不上,那老街其实也可以是手里拿着扇子,膝下靠着孙儿的慈祥奶奶。为什么一定要这两种女人?因为这样的女人总是包容、孕育、宁静,身上有股静谧的气息,就像哺乳中的母亲,但她却有着很多的故事。这就跟老街一样,老街也有着许许多多的故事,而我这个故事也是从一个老街听来的,是个有关女人的故事。我已记不起到底是生前听来的,还是死后,只是记得有这样的一条老街,老街上有这样的一间半木半砖的古屋,有一个女人总爱坐在门槛上,撕扯着她的头发,似乎不将头顶上稀疏的半灰白头发全都拔落不罢休,街里的人都说她是个疯子。从来就没有人因好奇而走到她身边去问她这样拔扯头发不疼吗,但心里的疑问总浮现在他们走过的时候;而她也当然不会主动的解释,只是裂着缺了门牙的嘴巴嘻笑着,唾液径自顺着嘴角淌下。
我其实很想去摸摸她的脑袋,但我担心她会因感到冰凉而吓着,便罢止了这个念头。听说她有个母亲和双胞胎妹妹,母亲不晓得是患上什么病来着现在待在医院里,至于她的双胞胎妹妹至今不知下落。据闻,她的妹妹很会念书,很早就拿了奖学金到城里念书去了,好像也回来过两三次,但在闹了这么一件大事后就没有音讯了。
实话说,我听的故事不下百个,但对这个故事始终无法忘怀,也不晓得我生前跟她们有什么瓜葛。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总嵌着这样一副画面,就是:有一个女子,长得白白净净地,她坐在一辆车子里,眼睛注视着流在车窗上的水珠,看着水珠在车窗上慢慢地凝集,当晶莹的分子聚成足够的重量后,随着地心引力向车驶的反方向垂落,形成一道道隐、现的水痕;每一点点的水滴都在重覆此类的行径,先隐、再现、后没,乐此不疲,而她也在计算着次数,不亦乐乎。她抵在车窗的前额载着冷漠,视线也忽隐忽现地,呼出的二氧化碳模糊了她的瞳孔。过了这座天桥也就到了,她在心里默念着。你问我为什么我会知道她心里想着什么?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她心里的想法,可能因为我是水鬼的因故吧!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答案,也不知道对不对,可能要找长老问一问)暂且别管原因,我还是先说说她心里所想的。
一直以来,她将这座桥定为老街的象征,看到它就意味着她将回到另一个家,她不愿意回的家。她现在的感觉真的是五味杂陈,我也说不出她现在的确切感觉——低落是有的,但有更多的是麻木,与她的年龄明显的不符。她似乎已学会让悲伤变得麻木,或转换成以麻木的方式呈现,似乎那样就不会妨碍别人,自己也不会陷入忧伤情境太久。停在车旁的轿车,一个女孩坐在少妇的腿上,少妇正为她绑理着长发,可她却直盯着她看,使她不免怀疑自己的哀伤是否让她瞧出端睨。小孩总是有洞察的天性。为了掩饰,她不自然的眨眨眼睛,试图一并把聚集的雾珠覆入眼睑。一切会恢复正常的,她念咒般的安慰着,试图抹去记忆里跟母亲唯一一次的共车情景。一直到今日,她还记得那女孩和少妇是坐在前座的。但她忘了为何会特别注意这个情节。对啊,我也不明白为何自己也一直记得这样的细节。算了,反正也理不出个头绪,我还是继续说我的故事好了。
小地方就是这么好,每一个人都很热情,对于谁家的事都了如指掌,丑事更是一日传千里,所以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在各人的泡沫中上映,所以我很喜欢老街,更喜欢老街口口“传闻”的故事,那是不用说故事者和听故事者负责任的故事。就拿这个故事来说好了,听村口庙祝阿华伯说是这疯女子隔壁家的阿花姨跟隔壁巷子的阿珠姨说的,他说(也不知是阿华伯说还是阿花姨或是阿珠姨说,反正说故事者愿意讲,听故事的人负责听就好)八九是跟那起杀人案件有关。
待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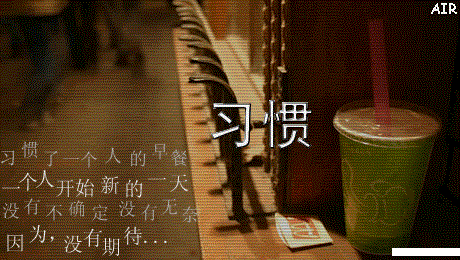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